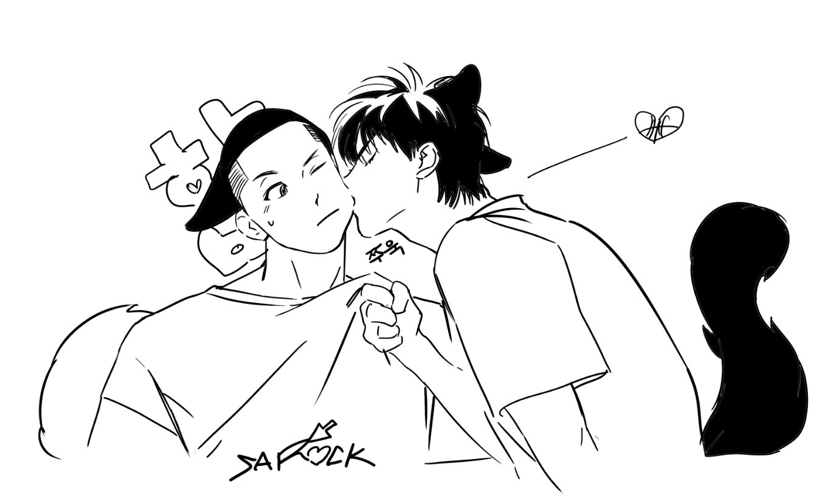
宇宙已经膨胀到临界点的消息,我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比起科学家的长篇大论,更让我有直观感觉的是,家里挂的母亲的照片变得模糊不清。她的脸庞像被水洇湿的墨迹,弥散成一片灰白的雾,再也无法辨认。物质与空间的结构愈发松散,许多东西变得面目全非。其实我早已忘记了母亲的样子,留下这张照片是为了某天提醒自己,但我从没认真看过。我想到,内心的承诺有太多永远不会得到兑现。
宇宙是一块在烤炉里不断变大的面团,我们是其中被牵引着远离彼此的葡萄干。路开始变长,时间开始变长。原本我拜访最近的朋友只要十五分钟,现在要走一天时间,开车也无济于事,活塞的冲程距离同样被拉长了。我朝窗外望去,昔日的城市不知所踪,外面成了一望无际的荒原。一天从24小时变成48小时,再到96小时,长到无法打发的孤寂时光令人难以忍受。我们迷失在辽远的时间空间里,越来越难遇见别的同类,仿佛是生活在远古时代的野兽,对自己所处的世界感到无比陌生。
我和邻居们先是用呼喊来联系彼此,我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守在窗前,只为了等待一声模糊而遥远的呐喊,无法辨认含义,但它是来自某个人的,某个再无法见到的人。之后,打电话成为唯一的联系方式,但就连电波传达的时间也越来越久,大部分时候,听筒对面只有漫长的沉默,长到双方都忘记了原本说的是什么,只能聊些不着边际的东西:
“我最后一次见到别人是在三年前。我走了一百五十公里才和她碰面。”
“这边的雨已经下了四个月,雨滴悬在空中,慢得能够用手抓住。”
我决定什么也不做地等死,因为做所有其他事都太久了,也太累。但这种等待同样遥遥无期,我甚至想,宇宙的末日和自己的死亡究竟哪个先到。至少在通向毁灭的路上,我并不孤独,这是我最后且唯一的宽慰。
在教育行业这么多年,这几天才慢慢体会到,之所以应试教育是国内教育的主流而它之所以那样设计,不是为了遴选能力最优者,而是要确保社会的管理阶层、精英阶层中大部分是听话、服从的无异见者,所以教学中,评估的地位大过学习本身(习得、理解、迁移),评估方式也只能是现在所见的那样,考试为主、客观题为主,主观题实际上也是客观题。与其说是在遴选学习能力强者、会举一反三者,不如说是要确保他们是循规蹈矩的,而“应试”之义不在于在学习结束后做总结性评估完成对学习者的反馈,而在于让评估本身成为目的,居于教育的核心,通过长达十二年的学习锻炼人服从规范、向它效忠的“品质”。而这条路上一旦有所成便难以主动放弃,这是应试这个单向的零和游戏训练出的心性之一。
在一个表面推崇优绩主义的体系中相信优绩主义的人,较倾向于服从体系内的主流价值观、默认这个体系中所有的主要条款、附加条款,而加入这个游戏前,我们甚至都没有机会浏览一下 terms and conditions 再按下 agree and proceed,我们往往无从知道what we have signed up for
魂器 @yqh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