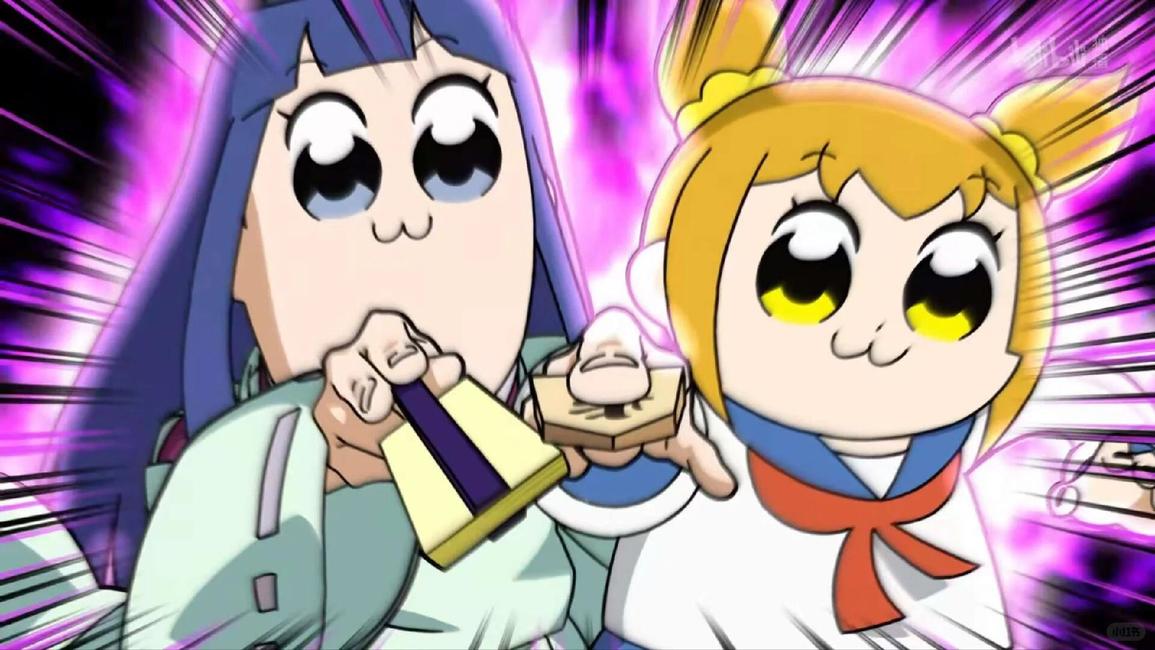
在纽约胡吃海喝一周的观感:纽约的小费文化(tipping culture)远远没有加州尤其是湾区扭曲。目前我去过的餐厅里,小到路边摊大到米其林,虽然都用 Square 等电子系统支付,但在结账时基本都没有默认选择高额小费,而是普遍让顾客自选小费额度,并且不给小费的选项(0%)不是在第一位就是在显眼可按的位置。很多中低档的小店,要么是结账过程中干脆没有让你给小费的选项;或者有小费选项,但他们根本不在乎你给不给:好几次我结账时,选择小费的界面才出来没两秒,我还没来得及伸手按,店家就光速把屏幕转回去,直接打印了一张没小费的收据塞回给我。我这几天在吃饭时都有暗中观察其他食客,很多不提供服务的自助餐厅(比如 pizza / bagel / deli)大部分纽约食客共识坚定,都是理直气壮选择不给小费,本加州土鳖看了,心里给桀骜不驯的纽约人民默默点赞。
反观加州小费文化就猖狂多了,首先别说餐厅了,加州现在但凡有电子支付的地方,连厕所都恨不得收你天价小费,我上次去投币洗衣店,连那个无人售货机都有脸问我要小费,闹麻了。其次,加州餐厅付款机的小费选项里,前排默认选项都是最高的 18%、20% 甚至 25%、28%,不给小费或者自己输入小费的按钮一般都被排在最后面,或者干脆被层层菜单选项隐藏了起来,逼你多重操作去找。每次当着服务员的面干这事,就像在国内病毒网站想关掉黄色页游弹窗一样的汗流浃背拆弹现场。注意:零小费的选项位置在哪是否隐藏,这是店家故意设置的,就是吃准了大部分顾客会在社死尴尬恐惧面前服软交钱当冤大头。最后,加州餐厅收银员还各个都跟大爷似的,小费给少了(在很多餐厅眼里 20% 都算少)还会忍不住喊麦顾客或者阴阳怪气一下,可能因为加州人都太怂太不缺钱太被欺负惯了,我经常在自助服务处(self serve / pick up)看到加州冤大头门排着队面对空气白给 20%+ 小费,小费常态化的罪魁祸首就是你们吧!
还有我最近发现加州人民在争当冤大头这个赛道有良好的自我管理意识:没人找他们要钱,他们都恨不得把钱全给别人。整天看到有湾区人在网上问一些月球问题:我该给理发师、干洗店、邮递员小费吗,我该给报税的会计小费吗,你们以后想干什么我都不敢想了,以后开庭了你们是不是要给法官小费??学学纽约人民,都是批斗那些阴阳怪气服务员的!劳动人民团结起来!
“女性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潜台词不就是“女性要提防男性,男性都是潜在罪犯”。不然怎么会需要保护自己。女性被路过的狗咬了,走路摔下楼梯这些新闻都不会有这个评论。但是一旦被男人伤害了,就会有这句话出现。“男性”这个词是潜藏在这句话里巨大的阴影,一个不能说的凶手,一个隐形的不被讨论的人。
但是这话不能说,明说了就是挑拨男女对立。
比伏地魔还夸张,人们用“他”指代伏地魔。但“男性”,却消失在人们的唇舌里。
他们把凶手藏起来,再聚焦在受害者的照片上,这样新闻就会被引导到女性身上,被议论的也只是女性。
人们很怕“全体男性”会成为众矢之的,他们会百般强调这只是个别男性所为。
但是对于女性,他们便不会这么粗糙不会这么敏感。他们会把一个女性扩大到全体女性。一个女性被害了他们便说“女性要保护自己”,一个女性撞车了他们便说“女司机懂的都懂”。
“父权”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性的东西,但“男性”是一个具体的就在身边的实物。
因此,讨论用“父权”是安全的。用“男性”是在挑拨男女对立。
就像男司机出车祸,“suv”“小轿车”总会用来指代“男性”一样,“伤害女性的男性”会被很多东西指代。
女性要保护自己✅可以说
女性要注意不被男性伤害\男性注意不要伤害女性❌不可以说,说了就是“挑拨男女对立”,就是在“伤害男性感情”,就是“你个疯子”。
明明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充满歧视的社会,种族歧视,全体女性歧视……但是主流大众没人想改,都在津津乐道,随口把歧视挂在嘴边。
但是到了“男性歧视”这里,⛔️就有许许多多规则了,每一条规则都在写着“此路不通,请绕道到歧视女性的路上”。
社会给男的很高的可信度,最近那个非洲洪水遇险自救的女生就是逃生后被困,在每个窗口期和救援联系,救援没去,因为救援认为女的在危急关头不可能冷静下来认清现实,他们觉得她只是在撒谎骗人去救她
《我说,所以我存在》
一本远远超出预期的书,只在台湾出版了,大陆没有出版简中版——实在可惜,考虑要买一本纸质版收藏。虽然在末页给出的标签是「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但读来的体验是「远远不止如此」——并不是想象中偏技术性的内容,而是谈论了相当多的议题,关注了各种边缘群体的境况,应该说是一本关于「社会不公正」的书,极有启发性。
作者库布拉·古慕塞是在德国的土耳其女性,既是「第二性」,也是被排斥和边缘化的移民,还是总受到误解和质疑的穆斯林。于是,女性的语言、土耳其的语言、穆斯林的语言都是被忽略和排斥的——被把持话语权力的主流群体。
最初吸引自己的是这本书开头的例子:语言将对应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亚马逊的皮拉哈人(Piraha)只有一、二和许多,没有其他表示特定数量的词汇,也没有精确的颜色用词。最奇妙的是,他们没有过去的时态,「他们是真正活在当下、专注于现在的人」。如果他们被问到在皮拉哈人出现之前、在森林出现之前情况如何,他们会回答「一切一直是如此」。「皮拉哈人陈述的内容只与此时此刻直接相关,可能是谈话者本身所经历的时间,或者谈话者生命中接触过的人亲眼目睹之事」。古慕塞问道:如果我们说着一种没有过去的语言,我们的思维还会同现在一般,投注在过往遥远所发生的事吗?还会沉浸在历史故事或他人的回忆中吗?这对宗教、思想运动和国家有什么样的意义?没有集体历史,民族国家可能存在吗?
皮拉哈人似乎在展示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其视线范围内只有当下、直接经验,稍稍遥远一些的间接经验都不是可信的——如果没有任何人目睹过,这件事就不存在于他们的世界之中。无法想象的奇妙体验。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在过度专业化的社会下,知识被割裂成无数不得不互相依赖的部分,如果不信任他人提供的间接证据,一切便无法运行。
「每种新语言就是一个额外的存在空间。我们这个世纪是人以一种以上的语言做梦的世纪。」不同的语言总有相当不同的体验,用英语和日语阅读和思考,似乎动用的是不同的脑区——读中文疲惫之后,读其他的文字仍然是舒适放松的。并不是母语的英语,似乎更「单纯干净」,或者说携带有的东西更少——对自己而言,是不携带有过多负担的轻便工具,说只是说而已。并且,又由于「异质性」的疏离感,更像是另外一个人在与自己对谈:更容易地能将自己分离成两个部分,以局外人的身份来看待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古慕塞关于「社会不公义」的分析,细致又有力:
**语言博物馆、有名者、无名者和标签。**无名者自由地游荡在博物馆之中,观赏关在笼子中的有名者和笼子上的标签。有名者是女性、黑人、穆斯林、性少数群体。「无名者想要理解有名者,但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集体。他们分析有名者,检视他们,将他们分类,将他们编目,最后给他们一个集体名称与一个定义。这就是个人成为有名者,并且被去人性化的时刻」。「透过无名者的眼光来看待有名者,他们没有个性,是集体的一部分」——女人有女人应该有的样子,黑人也有黑人应该有的样子,穆斯林也有穆斯林应该有的样子。
当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穆斯林可以是女性主义者?为什么黑人要跳芭蕾舞?……他们并不真正地想了解对方,并不真正地信任对方展示出来的样子,而只是因为对方冲击了「有名者的类型」,现有的类型不适用了。他们在审查有名者们,想要继续将有名者按照刻板印象的方式来归类,想要得到一个证实脑海中刻板印象的答案。「标签」是重要的,有名者的话是不重要的,有名者自己如何定义自己是不重要的。「刻板印象有如一件盔甲,但它保护的不是穿它的人,而是局外人的无知」。
无名的主流群体不需要解释自己,他们为自己独特的世界观起了名字:普遍、中性、理性、客观、公正、科学。他们对事物的观点有着最强大的名字:「知识」和「事实」。而有名的少数群体只拥有「意见」和「经验」。
**我是难民,我是所有难民。**我是少数群体面临的问题还在于,因为社会通过标签来认知他们,于是,他们不得不「代表」自身所属的群体。「如果我,一个明显的穆斯林,在马路上闯红灯,那么十九亿的穆斯林都跟着我一起闯红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和我一起漠视交通规则。」常见的表达是,当一个同性恋或者女性做了某件事,就会有「我就说同性恋/女性都是……」;而当一个男性、异性恋做了某件事情,没有人会将这件事情和整个群体联系在一起——因为无名的主流群体不需要标签,他们是作为个体活在世界上的。
Sara Yasin在《穆斯林不需要「善良」来获得人权》里写道:「我记得当我不再戴头巾之后的几天,我穿梭在人群之中,那种隐形的感觉令我漂染微醺。……我不需要无时不刻表现得和善可亲……我现在被当作独立个体了。我的每个失礼行为就只是我个人的失礼行为。但是,根本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之前不是如此?」
「我们可以不再教育出这样世代:将作为所属群体的完美代表视为人生的义务,随时准备好为他们存在的权力辩护,并且去满足观众似乎永无止境的挑衅胃口。」
**试图理解与自我解说是一种暴力。**「没有人能够每天都解释自己复杂的存在,很多时候他自己也完全弄不明白这一切,至少在不摒弃人性的情况下做不到。……人不可能理解一切。我也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要去登山。我也不必非理解不可。……如果有人想理解我为什么要戴头巾,我就会想,这背后有太多因素了,你不可能说理解就理解,因为那是一个过程,背后是一种生活。你怎么可能理解?」「你试试看让另一个人理解你:你的整个人、你的成长、你的矛盾、你的空军、你的希望。然后你再想想,你必须持续不断地这么做,天天如此。这是羞辱、耗尽、剥夺。……你要让一个排斥任何神灵的人理解你的信仰,这无疑是天方夜谭。」
尊重他人真实的样子,并不一定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每个人有自己的人性,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这就足够了。主流群体执着于让「笼子里的人」解释给自己听:为什么?为什么你奇装异服?为什么你不喜欢异性?为什么你不生小孩?为什么你不结婚?——但当你反问他们这些为什么的时候,他们无从解释为什么要有穿衣的规范、为什么喜欢异性、为什么要生小孩、为什么要结婚,他们只会恼怒,因为这一切都是「自然而正确」的,主流群体不需要解释。
**你被囚禁在语言与存在之间。**像前面说的,向一个不信神的人解释宗教信仰,用一种与信仰格格不入的语言来解释灵性等无法解释的事物,就像透过他人的眼睛看待赤身裸体的自己,我们是否还会认识自己?古慕塞也提供了更为世俗的例子:当你必须对一个不识爱为何物的人解释你为什么要和你的伴侣共度余生,你将你的爱合理化,强加一种语言和思维模式,希望对方理解。在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之后,你听到自己叹息说:因为我的伴侣给我提供经济保障。就这样,你的语言远离了你的感情,你的语言和存在之间分道扬镳。
这种「隔靴搔痒」的痛苦大约是语言的界限,也是心灵的界限。父母是「不知爱为何物」的例子,他们的词汇表里大多是责任、孝顺、义务、家族等等——于是在解释亲密关系上,可以说大家各自操持着不同的语言,鸡同鸭讲。
**语言学缺口。**没有名字的问题无法被解决,在性骚扰被命名为性骚扰之前,这种行为经常被认为调情乃至是赞美,受害者无法向其他人指明自己的经历,也无法采取措施来预防。语言学缺口将受害者留在无力的处境之中:受害者无法以言语表达问题,加害者不觉得做错了事,没有足够多的人可以觉察这种布工艺,无言、无能、无视。
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为之命名:有了名字,问题才能被看见、被讨论,最终被解决。隐形家务劳动同样也是一个例子,在拥有这个名字之前,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无时不刻的精力消耗很难被描述——要怎么向其他人描述这些细碎但是无时不刻在吞吃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呢?在谈话的对象是连家务劳动不做的男性时,事情就更糟糕了。女性的问题没有名字,「因为标识事物、归类结果、赋予生活意义,这些不只是男人的领域,也是他们权力的一种基本特色」(Dale Spender)。当命名的权力被男性把持的时候,女性的问题永远是没有名字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无法被言说的问题。
类似的,Allen Johnson在《性别打结:拆除父权制违建》中谈到了「被父权制定义的勇敢」,作为一个积极词汇的「勇敢」被定义为「父权式的阳刚」,而「冒着风险表达感情」「展现自己的脆弱」尽管是困难的,却不被认为是勇敢的。或许可以说,我们不仅需要填补父权制的语言学缺口,为女性的问题命名;也需要净化父权制的词汇库,当我们不得不使用这些词时,反思性地检视其内涵,并赋予其更为全面和多元的意义——否则,父权制将在词语的使用中被反复强化和再生产。
**被迫拥有的知识。**「伊朗、伊拉克、阿富汗,我任由全然陌生的人来规定我应当知道什么、我应该具备什么知识,只因为我头上的一块布,只因为我的信仰。……(似乎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才能为自己辩护。」
**少数群体是矿坑中的金丝雀。**发生在少数群体身上的暴行,总有一天会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古慕塞举了Mely Kiyak的例子:「在我十年前面仇恨邮件和评论的时候,我的同事无动于衷,认为这是少数群体的问题。十年之后,他们才觉察到仇恨的问题并描述他们,但他们宣称,以前没有这么严重。当然不是如此,以前也同样恶劣、恶心、野蛮,不过只影响到『我们』。」
**仇恨者决定了社会议程。**「透过对他们的挑衅作出大量回应,我们将他们合法化,赋予他们社会意义的位置。我们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反犹和反同提升为合法的世界观,提升为『意见』。我们让自己被告知每天该做什么事,生活因此被填满。右翼分子和种族主义者决定了我们的社会议程,指派家庭作业给我们,而我们乖乖完成。」
**刻板印象并非不真实,而是不完整。**如果一个故事主导了对整个人群的认知,那么这些人就不再作为个体存在。以类别来定义人不一定是错的,但是并不完整,一个事实变成了唯一的事实。克服刻板印象的方法,就在于「听」,真诚地去听到个体的故事,去见到人的多样性——当人们向你展示自己时,信任他们。
**像多数群体一样自由发言**。自由发言预设了一个人的存在、人性和生存权不受威胁,不需要去捍卫或者证明什么。用越南裔美国作家Viet Thanh Nguyen的话说:「来自少数族群的作家,写作时要表现得好像你是多数族群一样。不解释。不迎合。不翻译。不道歉。假设每个人都知道你在说什么,就像多数群体表现的那样。以多数族群的特权来写作,但也带着少数族群的谦逊。为什么要带着少数族群的谦逊?因为被羞辱的人通常没有学会何为谦逊。因此,当无权势者一旦掌握了权力,往往会滥用权力。不要变得和多数族群一样。要变得更好、更聪明。谦虚,但依然有自信。」
**平等与多元化带来更异质化的生活。**不要浪漫化平等和多元。平等和多元化不是为了让社会更加和谐、更有共识,而是导致更多的异议和重新协商。多元意味着接受少数群体、边缘化群体以及所有的潜力和所有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将是「我们的」问题,「出身迦纳的高收入男性医生和出身意大利的女酒鬼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最后,永远不要适应。
「犹太哲学家Abraham Joshua Heschel写道:『我想谈个人,如果一个个人停止感到惊讶,那么他等同死了。……如果我看到一件恶行,我不会冷漠以对,我不让自己习惯我碰见的暴力,我总是对这些事情感到惊讶。因此,我反对暴力;因此,我可以用我的希望来对抗它。我们必须学习感到惊讶,不要让自己适应。我是社会中适应力最差的人。』这段话让我联想起印度哲学家Jiddu Krishnamurti的一句话:『适应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并不是健康的表征。』
我不知道要怎么办到永远不停止感到惊讶,永远不习惯不公义,一直展现你的团结并时时警惕,但却同时过你的生活,在生活中找到了乐趣并走自己的路。」
【更新:三人均被捕】
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港足今晚在大球場主場對伊朗,據現場球迷指,賽前奏國歌期間,大批黑背心警員在場拍攝觀眾席,半場前在看台帶走三名穿紅衫的港隊球迷,分別是兩男一女,他們涉嫌違反國歌法被捕。
據了解,被捕兩男一女年齡由 18 歲到 31 歲,在奏國歌時其中一人無企起身,另外兩人擰轉面,三人因涉嫌違反國歌法被捕,案件由灣仔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
https://www.instagram.com/p/C74HFfLBt3f/
「大家好,6月15日,将是我们亲爱的朋友雪饼被恶意抓捕的1000天,也是雪饼开庭未宣判近9个月的日子。
这过去的日子,不管你认识或不认识雪饼,相信每个身处其中、听过她们故事的我们都很煎熬,也很心痛她们两人在里面的煎熬、折磨、甚至身体的摧残。尽管在墙内、社交媒体上已经越来越难以传播关于雪饼的故事,也难以传递太多资讯给到雪饼,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努力、再努力地把我们对雪饼的想念被听到,更希望她们有朝一日重获自由的时候,可以看到、触碰到我们对两人的思念和爱。
所以,雪饼的朋友建立了这个留言网页(链接附后),希望知道或者听过雪饼的朋友可以留下你的想法、感受与爱,不了解雪饼的朋友也可以进入到这个页面了解她们的过往。
同时,也希望你可以帮忙传播这个留言网页,分享链接或者海报到你的社群或朋友圈中,让更多人可以留下对雪饼的思念,期盼雪饼平安。
留言网页(連結在中國可以訪問;限於嘟文發表之時及之前,之後不清楚):<https://padlet.com/freexqjb/padlet-nxu526duh8hjm6y>
释放雪饼网站(連結在中國訪問需要非常規手段):<https://free-xueq-jianb.github.io/> 」(連結在中國訪問需要非常規手段):<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08703.html>及<https://x.com/FreeXueBing/status/1798579022466842797>
-分割線-
聯繫嘟文:<https://me.ns.ci/@zaijianghueryuanjianghu/112879625068803231>
<https://me.ns.ci/@zaijianghueryuanjianghu/112627316475459126>
<https://me.ns.ci/@zaijianghueryuanjianghu/112615641964416611>
<https://me.ns.ci/@zaijianghueryuanjianghu/111107450394854487>
<https://me.ns.ci/@zaijianghueryuanjianghu/111125432245277402>
<https://me.ns.ci/@zaijianghueryuanjianghu/109866795779548121>
<https://me.ns.ci/@zaijianghueryuanjianghu/109795369976104163>
这世界上最厌女的地方就是政治。埃隆马斯克这种奇行种男都可以随意点评政治,泰勒斯威夫特这样人美心善的大好人只因为表达了一下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被指着“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左右政治”,害怕自己表达政治观点被封杀。现实都这样了都还有男人攻击我“政治没有排斥女性哦,我们支持男女平权”。好的,那我宣布下一节美国总统泰勒斯威夫特来当,反正比那两个难看的老头强,我看他们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说实话,地球上所有的男性领导消失,世界只会变得更加光明灿烂,地球直接全面北欧。谁都不需要run了,北欧就在家门口,run什么run呢?我建议男人们抛弃成见与我们一同摧垮父权制,否则你所做的革命不过是给他人送了嫁衣,因为男性政治圈最喜欢搞那种出尔反尔肮脏卑劣的尔虞我诈还美其名曰“政治手段”的下三滥套路,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前几天看了个十几分钟的本地人纪录片,就是那些被送到寄宿学校,然后被文化剥夺,被虐待,若干年后发现上百儿童骸骨导致加拿大新出来一个谅解日的官方节日的那些本地人。是个上了年纪的女性,口述当年在寄宿学校的经历。非常轻描淡写,时不时的还呵呵笑了出来。
好比说,他们打我们,因为我们讲自己的语言,因为一些小事,或者就因为他们心情不好。呵呵呵呵。
还有,他们经常给我关壁橱里面,然后把我给忘了,呵呵呵呵,最后我自己打破壁橱跑出来的,呵呵呵呵。
这种状态让我想起了我妈妈家的那些亲戚们,就是很多听起来特别特别特别惨的事,她们说起来就是,呵呵呵呵。轻描淡写,然后呵呵呵呵。
难过吗?悲伤吗?愤怒吗?也许有也许没有,但是苦难的当下,并不是感受苦难,而是走过去。
事后提起来,也就平铺直叙的讲出来,然后不造如何评价如何表达情绪的时候,就呵呵呵呵。
那个影片的最后,讲述人说,我希望像姥姥一样,穿着叮叮响的裙子,舞过长廊,回到我的家。
影片的简介说,讲述了当事人痛苦的经历和最后的谅解。
看完我就很想说,谅解你xxxxx
这种口述历史,我都想给妈妈和老家那些人拍一个了。
最后条条道路都通往恐怖。卡夫卡的妹妹们跟他的许多朋友一样都在集中营里遭到杀害。1941年10月21日盖世太保将自1939年起守寡的艾丽强行运往洛兹送进犹太人居住区,10天后瓦丽和她的丈夫不得不接踵而至。1942年春,纳粹当局分给艾丽一所窄小的住房,妹妹和妹夫以及最小的女儿汉娜也搬来居住。1942年5月洛兹发生多起枪杀犹太人事件,11000名犹太人死于非命。自这一年年初起德国人就杀害了7万名犹太人居住区居民。卡夫卡的妹妹们估计在1942年9月死于毒气室,汉娜·赫尔曼的踪迹1941年年底就已经消失。奥特拉起先由于与约瑟夫·大卫的婚姻而受到保护,免遭迫害。然而1942年8月大卫与她离婚,从而冷酷无情地丢下她不管。还在当月奥特拉就被放逐到泰莱钦。1943年10月她自愿当护理员护送一列车犹太儿童到奥斯维辛,估计她清楚地意识到这意味着死亡。77297个犹太人在波希米亚和梅伦被德国人杀害,死难者的名字今天铭刻在布拉格平卡斯犹太教会堂的墙壁上。在卡夫卡的妹妹们的家庭圈子里,除了汉娜·赫尔曼以外,只有女儿们——格尔蒂·赫尔曼、玛丽安妮·波拉克、薇拉和海莱娜·大卫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费利克斯·赫尔曼1940年在逃往法国的途中死于一次发烧感染。他们留下的那些显得宁静而和谐的出自世纪之交摄影室的照片,由于最终惨遭迫害的人生道路而看上去像一个已沉没的世界的无声的象征,这个已沉没的世界的居民当初没能料想到,怎样的灾难将会降临到他们头上。
我走向你像走向一条河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