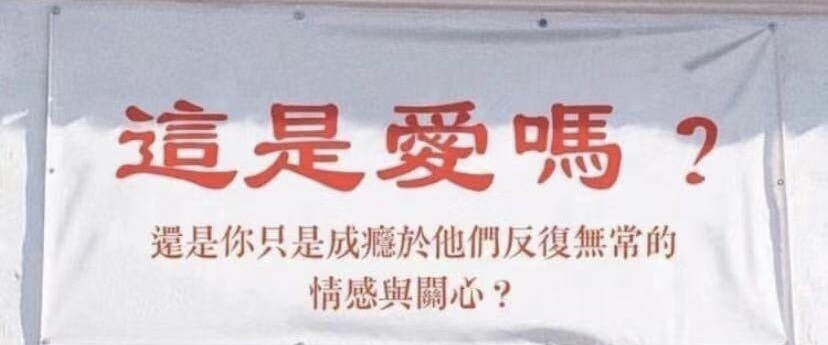
其实倒不是极权特征,香港从疫情后也常有这样新闻:铺头经营困难、房东不愿降租,于是租客退租、关门,不少还是老店名店,空几个月运气好会有新客,但新价格直接斩头斩胸。
朋友说(不一定对)原因是香港的房东也多是守着祖产快活度日,对现实缺少认知,也懒得同情租户。
非要说有啥共同点就是二代和大机构和笨重体制一样缺少感知现实和及时反应的能力。 有的是不能有,有的是不想有、不需要有。
开始看周轶君的《中东生死门》,连续看了好几个人肉炸弹报复轰炸的循环后,看到的第一个普通生活故事是……
作者和同事在安息日的晚上,在街上遇到一对犹太教徒父子,对方非常艰难地用几个英语词和她沟通想请她们帮忙——安息日禁止动电器,但他们家跳闸了,所以要找非教徒去帮他们拉电闸……老头还解释说“不是所有犹太人都这么守规矩。”
作者和同事帮他们拉起电闸后又帮他们拔掉空调插头避免空调全天运转。老头跟她们说他们原本准备去附近的咖啡馆找阿拉伯厨师帮忙,一般这种事都向阿拉伯人求援。
也太自欺欺人了吧‼️
(忍不住想起前一阵看文艺复兴时期八卦,书中时常有类似“XX尽管五毒俱全但他十分虔诚”的描述,到底虔诚在哪里啦!)
所以伦勃朗绝不是一个笨拙、不识字、缺乏良好教育的男孩。他接受了荷兰省最具学术性的城市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教育。在他的一生中,他的作品都有着强烈的文学激情,充满了对文本和图像的渴望。的确,与鲁本斯相比,伦勃朗没有刻意去突出人文主义者的风度,没有动不动就写下拉丁文的诗句,更不会引用维吉尔的诗作来润色他的信件。1656年,他的财产被列入破产法庭的物品清单时,其中并没有包括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即便如此,在那个时代,没有哪个画家比伦勃朗更有书卷气,或者更准确地说,更了解《圣经》的经文;没有人比他更痴迷于书的重量(无论是道德层面的还是材料层面的重量)、装订、书扣、纸张、印刷和故事。如果这些书不在他的书架上,它们肯定无所不在地出现在他的绘画和版画中:高高地堆在摇摇欲坠的书架上;颇具权威地躺在传道士或解剖学家的桌子上;紧握在雄辩的牧师或沉思的诗人手中。没有人能比他更好地描绘羽毛笔放在纸上,即将开始写作的时刻(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个过程会持续好几个小时)。尽管阅读在伦勃朗同时代的人当中很受欢迎,但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把阅读描绘成一种强烈、神圣而专注的行为。他画的一个老妇人,通常被认为是他的母亲尼尔特根,但其呈现出的形象肯定是年老的女先知亚拿,她在基督诞生的那段时间里“昼夜”进出圣殿。伦勃朗在这幅画中依照莱顿风俗,展现了她深深沉迷于《圣经》的样子。亚拿对鲁本斯也很重要。在《下十字架》的右侧画板中,他将她与大主教西缅放入了同一个场景,因为她也认出了婴孩耶稣就是救世主。对于鲁本斯来说,照亮亚拿的光源当然就是基督的身体;但对于伦勃朗的亚拿来说,光辉则出自书页。
图注:伦勃朗,《正在阅读的老妇人》,1631年。木板油画,59.8厘米×47.7厘米。阿姆斯特丹,荷兰国立博物馆
『TabBoo:利用厌恶性条件反射(惊吓图片和音效)来预防上瘾[Chrome]』
TabBoo 是一个 Chrome 扩展,它会在你浏览指定网页时,随机出现惊吓图片和音效,让你产生厌恶性条件反射,从而开始反感这些网页,预防上瘾。@appinn 有点离谱的扩展。但,似乎又说的有点道理
……
阅读全文: ![]() https://www.appinn.com/tabboo/
https://www.appinn.com/tabboo/
在网络上待久了很容易会忘记“人是复杂的”这件事。
最近在一家成人培训工作室实习社媒岗,主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澳洲中年白女,支持自由党,讨厌租金限涨法(澳洲9月份的新法规定租金一年内只能涨一次),反对接种新冠疫苗,因为去东南亚出差可能买不到她常喝的澳洲品牌牛奶而焦虑,甚至还有一次问我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吃狗肉。
按道理来说,遇到这种政治立场天差地别的人,我不跟她大吵一架就不错了,更别说在这干下去了。
但奇怪的是,除了上述政治问题之外,在她这里的工作体验其实非常好,甚至比我在任何一个政治观念相和的公司实习体验还要好。我之前曾经在一家香港劳权NGO,一家澳洲本地左翼社群媒体和一家国际中文媒体实习过,后两者还好说,只是不给工资工作比较累而已,劳权NGO真的烂得彻底,完全没有实习培训不说,干的是全职的活,我离职那一天立刻删光了主管联系方式。
澳洲的实习是按惯例不发工资的,于是她给我的工作量非常少,连dirty work都算不上,每天统计几个客户反馈表和上传几个视频就差不多了,会产生经济效益的工作她是绝对不会让我做的,视频多剪一个步骤她都要喊停,因为多做一步就需要付钱,而我做的是免费实习,是来学习而不是参与公司效益生产的。而她如果有需求要让我继续剪辑,也一定会按照市价给钱(她给另一位专业做剪辑的实习生就是付钱的)。不像那家劳工NGO,让免费实习生给她设计商品图,我真的无语.......而且她每天都会请一杯免费咖啡,我在左翼媒体干了三个月早班,离职前最后一次才享受到这待遇。
而且我说会有朋友来澳洲玩之后,她在工作时间帮我安排旅程,从酒店到餐馆,再到景点适合出行的时间,她都帮我一一选好,非常细致。
我跟她用餐时聊到中国年轻女性不想结婚,我如果在中国连恋爱都不会想谈之后,她很快就说:“那你来澳洲可以随便谈喜欢的!谈到澳洲人还可以婚绿留下来!”这句话真的是有震惊到我,因为她是第一个鼓励我婚绿的澳洲人,之前遇到的澳洲左翼,无论有多左,谈到中国人婚绿都是微微有点鄙夷的态度,好像要占他们便宜一样。
和她相处之后,我最大的感触是,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很多时候并不会影响你和这个人的相处感受,而一家公司的立场也和其对待员工的态度没多大关联。我在澳洲目前最好的工作体验居然是从一家右翼白人为主的工作室获得的,如果自己没经历过我也绝对不会相信这是真的。
没有预警,就像你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遇见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