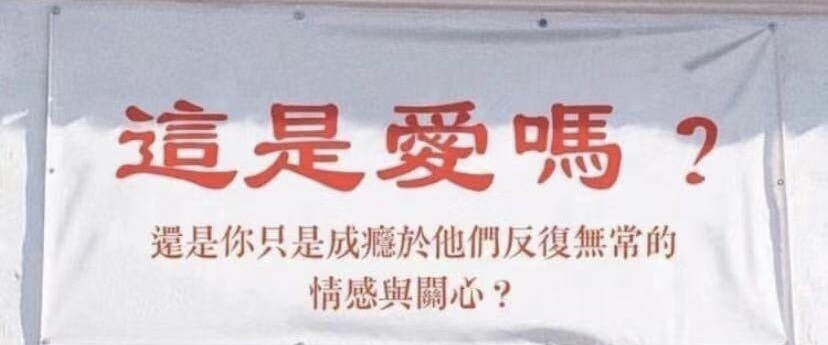
陪朋友带三个猫去宠物医院,进门就看到一个知性美丽温柔大方的长毛奶牛猫款款走来,绕着我们闻了一圈,非常熟练地蹭人,躺倒,打滚。大夫介绍这是客户弃养的猫,一岁多从楼上掉下来,主人不要了,他们治好了就一直养着,现在四岁多了,就在医院上班,因为亲人,平时主要负责安抚患猫家属情绪。介绍的同时带来的三只猫一直在扯着嗓门大叫狂叫,往死里叫,此起彼伏声震寰宇,骂得巨脏比逼格还脏,猫大夫过去闻闻,又回来看我们,疑惑地问咪?。。。平生头一次在一个猫面前体验到汗颜的感觉
(大夫玉照,忘发了补上)
受不了这些人觉得野猫闯入自己家中吃自己喝自己大摇大摆还不让摸是不知好歹,不懂报恩
野猫是真正的无产者,它只是发现了这片物产丰富的土地,树枝只是掉在了地上,怎么就变成容克地主阶级的东西了?我捡起来,怎么会是林木盗窃之罪呢?饭放在我野猫发现的地方,那就是我野猫的,怎么变成你给我的?你们真的是马克思主义下长大的人吗,你们这些吝啬的小地主?
邻居是个钓鱼佬,送给我家几条活鱼吃。我爸说不杀生,打算把鱼放生到公园里的大湖去。但是等我们放生的时候,有三条已经死了。
现在想,把死鱼和活鱼一起倒进湖里就行了,让死鱼回归自然循环。但是当时没经验,只把活鱼放了,回家对着死鱼发愁。
我爸说要不还是把死鱼放冰箱里,炖汤,我说也许已经死了半天了,还是不要吃了。
第二天早上,我爸终于想到了解决方案,让我趁上班前把三条鱼埋在院子里,和大白猫埋在一起。
我不愿意,说把鱼堆肥种蔬菜就行,或者扔到厨余垃圾也行。我爸说扔厨余太不尊重,因为“鱼是朋友,不是食物”(出自《海底总动员》里的吃素大鲨鱼)。
最终我给埋了,埋在大白猫隔壁的地里。我爸说他不在大白猫的地盘种菜,现在又多了鱼的地盘,导致他两块地都不能种菜了。我说大白猫和鱼不熟,它们四个倒不用合葬。
我把鱼埋得尽量深一些,以便日后还可以种菜。
因为我们放生得不及时,三条鱼缺氧而死,想必是我爸心怀愧疚,执意把鱼体面地埋了。
可是我觉得我们和鱼又不熟,鱼也不在乎人类的礼节,随便怎么处理,只要它们回归大自然就行了。葬礼是给活人的仪式。我想大白猫也不在乎人类的礼节,只是我们活人想把它留下,才把它埋在院子里,大白猫做了我们人类葬礼的主角,是它在照顾我们。
顺德特色的水牛奶制品:双皮奶、姜撞奶、牛乳片等等,已经很出名。当地有很多很多甜品店,制作这些水牛奶食物。
其中一家老字号的失败原因:老太太经营了一辈子,手艺极好,口碑极好。她七十五岁之后,干不动了,传给儿子。儿子儿媳经常吵架,儿子总想一夜暴富,不知投资什么东西,败光家业,儿媳心灰意冷,离婚走人,店也倒闭。
另一家老字号的成功经验:从太祖婆婆那一代起,坚持顺德人【女子不落夫家】【长姐当家】【传女不传男】的优良传统——五代人的奶制品手艺只教女儿。
1949年以后,没有【不落夫家】的习俗了,媳妇嫁入婆家,婆婆遂把独门秘方教给儿媳。
未必每个儿媳都爱她的丈夫,但儿媳算了算账:虽然丈夫不好,但婆家的祖业传给我,核心技术传给我,又舍不得孩子——看在事业、财产、独门秘技和孩子的份上,不离婚了,认真把祖业发扬光大。后来小店变连锁,连锁变企业……
【以上故事是真,但我的意见纯属笑话,搞民营企业的人不要当成经营指导】
认真:去顺德旅游的盆友,别在甜品店点“水牛奶”,全是制作双皮奶的剩余料,反复煮开、反复把奶皮刮走之后、倒回桶里的剩奶水。
想喝真水牛奶,去找批发零售生牛奶的店,他们用塑料袋装给你,很脏很脏。回去烧开才能喝,脂肪奶皮极厚,煮一次,锅子洗一个星期都洗不干净。
#Wut_a_beautiful_Duwang fun fact一则: 虽然很反直觉, 但仗助和亿泰同级不同班!
仗亿出双入对, 每天形影不离; 然而你皮近日重看《山岸由花子坠入情网》篇, 荒木老师早在32卷就告诉读者: *in mega mic* due 2 some unfortunate circumstances, 仗助和亿泰不在同一班:
这天放学, 仗亿溜溜达达到了站前广场, 忽然碰到一个女孩子约见康一. 亿泰特别八卦: "喔! 有戏看了!! " 然后扯着仗助躲到一边, 在墙角探头探脑: "欸, 怎么有点儿面善, 这好像是【和我同班】的同学啊? " (图一) 他不仅强调【和我同班】, 还报出由花子的全名, 给出了非常完备的信息, 就像仗助【根本不认识她】一样——如果仗亿同班, 那么亿泰默认两人都见过她、对她的名字也有大致印象, 说法应该类似"【咱们班】的山岸", 或是直接省略这个定语, "这不是山岸嘛! " [注]
更有意思的是, 接下来两个当事人一番拉扯, 康一以为对方想换班值日(图二上部), 由花子自承"每天都在关注你"(图二下部)——只有同班同学才有这种视角. 即葡萄丘高中的这届新生里, 亿泰、康一和由花子同班, 喷上裕也在其他班级(仗助和康一不认得他), 转来的未起隆暂不清楚, 仗助有意无意被"孤立"了.
但是没关系, 荒木老师自有安排, 两人会串教室找对方! 四部至少出现两次二人坐在一间教室里, 分别出自37卷和38卷, 挨得非常近, 说明频次足够高. 第一次明确在午休时间, 胖重中了枯萎穿心, 用最后的力气跑到高中部, 去向二人示警; 教室内两人有说有笑, 非常亲密(图三).
第二次是康一发觉由花子不对劲, 去找两人帮忙. 这次迷惑性非常强, 因为康一行色匆匆, 像一个忽然闯进来的"外来者"——这里"一动两静", 读者很容易误以为康一从外班来, 来找本就在一起的仗亿. 而且它展示的是【日常】中的日常, 一个普通的【课间】场景. 班上其他人在看书、擦黑板, 还有几个扎堆聊天; 而仗亿大剌剌坐在窗台上, 正悠哉悠哉享受【课间】: 两人并排坐着, 一个朝里, 一个向外; 一个喝着牛奶, 一个看着漫画, 太悠闲、太自然、太习以为常了, 怎么看都是【同班好友】.
所以我说荒木老师了不起, 写这俩一起上下学没什么, 一是为了剧情服务, 二是他们是邻居, 两家相距不到五十米. 可这两个分镜画来, 只为讲两人的亲密程度: 午休时间要串教室说话, 课间最多一刻钟, 也要特地跑到另一间教室, 除了"黏在一起"我想不出更合适的词. 两人的状态非常松弛, 特别像想到什么随口扯两句, 说完又各干各的, 或是干脆sitting there doing nothing. 写角色到这个地步, 你皮吓得纳头便拜!
注: 关于"因共享信息而省略句子成分". 交谈和对话是为交换信息, 最初对话会非常完整; 以仗亿出学校买饭为例, 我试着还原一下:
—有什么好吃的吗/今天吃什么好?
—幕之内便当/St. Gentleman家的三明治就挺不错啊!
—好! 尝尝去!
而当两人共享的信息足够多时, 对话就成了提示词; 即随着时间的推移, 对话会越来越简短. 比如开学两个月后, 仗亿再想出去吃, 对话极有可能变成这样:
—*脑袋往想吃的那家方向1摆* 走?
—走!!
【每日空谈误国】
推荐大家去听一下这一期不明白播客。
我以前对藏人和藏区文化完全没有了解。
说来惭愧,在听这个节目之前,我对藏区的理解还是你共灌输的那一套。也就是“在你共接手西藏之前,西藏由一群极恶劣的剥削阶级统治,他们无恶不作,贪婪暴虐,藏人被他们虐待得民不聊生,直到你共入藏之后,农奴翻身把歌唱……”
在亲眼看到你共的作为之后,我对你共的一切都有怀疑,但也没有怀疑过你共对新疆和西藏的统治,我没有看过新疆人和西藏人。也没有听他们说过话,不懂他们的风俗,也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我却觉得你共的所有恶,都是只对汉人的。
BBC发节目,说新疆正在建立集中营,维吾尔人在被文化灭绝。我知道这又是你共造下的一个罪孽,但我的“知道”只是一种理性上的理解,并没有深入到情感和生理的层面。
我也未能摆脱身为中国人的汉族中心视角,我总觉得他们是外族人,即使他们和我们一起被你共压榨和虐待,但就是隔了一层障壁,痛不到自己身上。
直到这一期节目给我介绍了藏人的学校为止。
我以前教过书(虽然时间很短),知道完全按照你共的教育方针来办的学校是个什么样子,在这种学校里,“教育”和学生老师都无缘,人能接受的只有不间断的灌输和宣传,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迫害。
但藏人的学校却很新奇,他们会教逻辑学(虽然也是基于宗教的逻辑学,他们叫因明学),他们会教天文学,因为藏历和汉人的农历不一样,他们要学会算自己的历法;他们还学计算机和影视制作,他们会自行组织活动,会搞辩论赛,甚至会自行创造藏语的新词……虽然只是一所”技术学校“,但说实话,这种自由的风气和重视实用,摈弃党八股的做派,是让我这个自诩”重视教育“的汉人都感到羡慕的。
然后呢,这个学校被你共给关了。
你共在西藏实行的是怎样的做法呢?他们要禁止藏人学藏文。
两相对比,我觉得我完全能理解为什么藏人会那么讨厌你共(希望藏人讨厌的真是你共而不是汉人吧,我觉得如果藏人真的讨厌汉人,汉人也没有申辩的借口,你共不就是由汉人组成的政党吗?),这种之前的高度和现在的情形组成的落差,任谁都受不了。
而且,藏人受到的这些限制我也觉得荒谬到不能理解。
谁能想象,在21世纪的地球上,藏人要被禁止去拉萨,汉人反而可以随便进去?
又有谁能想象:在21世纪的中国,支持藏文输入法的手机居然是苹果,没有一个中国的手机品牌会支持输入藏文。哪怕藏文是中国法律规定要写在人民币上的文字。
把别人的宗教圣地强行开发成旅游景点,不让本族人进去,又要灭绝别人的文字。
说真的,上一个以这种手段对付汉人的好像是日本鬼子吧?
说来也怪,我在听这一期播客的时候,想到的是小时候看的《还珠格格》。在香妃被进献给乾隆的时候,太后看香妃穿着外族的服装很不高兴,硬要她穿旗袍,后来是乾隆下令才阻止了这件事。
我记得当时我看这个情节的时候,只觉得乾隆真是一个英明的领袖,体贴的男人。
但现在一想,我觉得这个情节更像是一个悲剧:在一个皇权社会里,连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都要被约束,仅有的自由也是视皇帝心情法外开恩的殊荣,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该有多痛苦?
然而,至少乾隆没有禁止藏人用藏语吧?
希望藏人和藏文都能坚强地挺过你共的暴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e8WBpkjWjg&list=PL6oiB4RIxJB7qpKj4NscedHTnRSOhB6hC&index=111
没有预警,就像你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遇见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