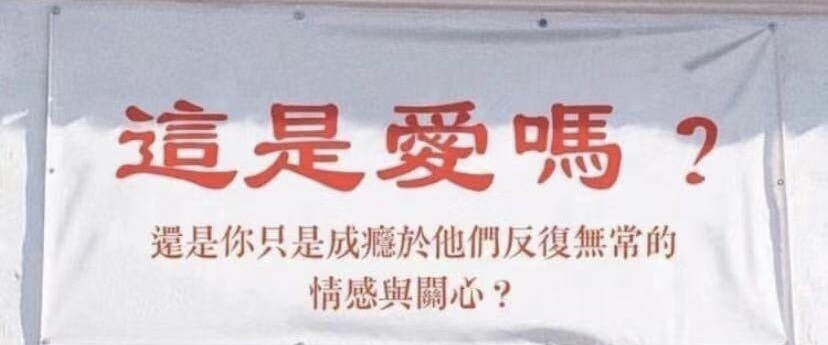
@board
重要通知:请元宵节晚上赏月的同志把赏月费打款给我账户里,每人16元。收费依据是按传统规定:十五的月亮 16 元。
开始听痴人之爱最新一期聊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主播半开玩笑地说小时候读(男作家写的)以女性为主角的世界名著常常都是类似的套路:有一个很美丽的女的(optional她还纯洁/善良/勇敢),她遇到了一个男的,她又遇到了一个男的,她可能还会再遇到一个男的,然后她悲惨地死掉了;这个异性恋的女的,为男的要死要活,最后不得好死;而那些不得好死的结局又升华了她们为爱献身的“女性气质”,让她们成为了文学史上被津津乐道的经典女性形象。除了《苔丝》,还有《巴黎圣母院》、《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等等。
听得笑死,忽然联想到在艺术史课上几次提到但一直没读的Lynda Nead写于80年代晚期的Myths of sexuality: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in Victorian Britain。这本书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经常在维多利亚时期绘画中出现的堕落女性/fallen woman是一个被男性艺术家“发明”出来的形象,并非先在现实中存在然后被艺术家“捕捉到”的。“她”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对于妇女可能获得更多权利、脱离掌控的anxiety、作为一种道德教化的“寓言”。“她”在画面中经常以衣着华丽的尸体形象出现,暗示death is the price for immorality。与fallen woman形象对应的是贤妻良母/angel of the house,也同样是被“发明”出来的。(此处再次有Griselda Pollock和Roszika Parker的“艺术不是镜子”论:art does not reflect women’s lives but constructs a stereotype. It is perspective, not descriptive. Moreover, art and culture reproduce patriarchy, playing an active role, rather than simply reflecting social relations.)
在这个角度上,文学和艺术还真是互相呼应手拉手。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手拉手:那些关于fallen women的绘画的target audience并不是画中经常被描绘的下层女性(包括交际花),而是中上层的人,正如我猜测哈代的《苔丝》也不是写给苔丝那个阶层的女性看的。)
了解ADHD还经历了如下心路历程:
了解到ADHD容易忘事
从小被说老了以后会得阿茨海默,原来不是,我只是ADHD!嘿嘿
继续了解
了解到ADHD患者是阿茨海默高危人群
告辞
没有预警,就像你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遇见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