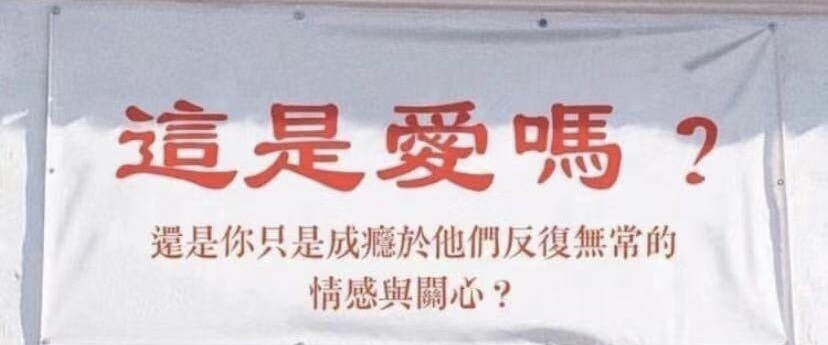
CW 厌女,审美霸凌,body dysphoria
不管是谁说“女人的身体就该如何如何”,我都很想说:我的身体不是你的政治游乐场,不管是说女人就该纤细柔美的、还是说女人就该英武强壮的,不喜欢“我必须要改变自己的身体才能符合、满足某种政治理念下对女性要求”的思路
想一想就觉得很悲哀,所谓的“弱女审美”和后来被推崇的“强女审美”,没有哪一个是不要求我去“美”才算是合格女性的,越是追逐就越是觉得,现代社会其实容不下一个真正的普通人、穷人或者“丑人”
最近发现低精力状态减少做家务痛苦的一个 #生活小技巧 :让洗衣机陪自己做家务。
多堆点衣服裤子床单被套什么的,让洗衣机慢慢洗,与此同时自己做点别的家务。有种“我不是一个人在干活”的自欺欺人感,和“至少坚持到洗衣机停工吧”的共患难感。
真的太幽默了,小红书给我推送一个自杀留遗言的帖,评论区好多人说要一起走,然后有个人坚持不懈地给每一个说想死的帐号留言,说走前帮我撸个小贷
刚刚看到三联记者这篇公众号文,讲到自己采访小红书红人,结果发现对方身份经历皆为捏造的事。荒诞之中也觉得是必然:
https://mp.weixin.qq.com/s/4FiJfzuzCYqESZZ8y1IdUA
类似的捏造身份却未能及时被识别,报道当真发出的情况也肯定存在。即使身份真实,依然有可能存在捏造的经历或夸大描述,尤其是在网络上高频发布过于典型的、迎合公众期望的表达,都是很可疑的。
在仅有的被采访经历中,我回想自己当时表达的内容,都意识到仍然很不完整,如果仅凭有限的内容发布,极可能给看报道的人造成一些误解。虽然那样呈现的可能更符合公众的某种理想预期,实际上却掩盖了现实的复杂性。
但如果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是很难识别出来与现实的偏离的,这其实也要求受访者自身首先就得足够自省,而这样的自省又可能影响受访者接受访谈的积极性。
这是采访必然面临的两难,在网络“人设变现”诱惑越来越大的趋势下,恐怕这样的事还会越来越常发生。
那么,医疗系统借反腐名义搞的小型文革,怎样导致医学水平倒退再倒退呢,举两个广东省内的案件:
医生甲,是某种儿童罕见病的顶级专家,带着国际一流的理论和国际先进的诊疗方案,医院重金聘请回来的。她收治一个小朋友,她以为用那套“先进方案”即可,她告诉孩子父母:某种药,去哪里哪里买。
孩子父母发现这药很贵,而且医保不给报销,遂举报医生甲串通药厂、收受贿赂、故意忽悠他们买自费药。
原本这种举报,当局不怎么爱管,然而医生甲所在的医院那年恰好得罪政府,正在接受审查。医生甲因为是空降来的专家,资源都往她和她的小组身上倾斜——这些年,国内事业单位和科研机构的晋升通道非常狭窄,同行们面临非升即走的失业威胁,能“搞掉”一个老家伙,就能空出一个位置,大家听闻她出事,纷纷落井下石,检举揭发她的所谓违纪行为。
然而患者父母和同行检举的黑材料,纪委无法证实真伪,医院只给她内部处分。她虽然没有落得疫情期间李文亮、时军、艾芬医生的下场,但调离科研岗,并且不准行医,最后不知调去什么地方当办公室职员。
其他医生看在眼里,不想蹈她覆辙,从此决口不提这种儿童罕见病的国际先进治疗方案,胡乱开点能报销的便宜药搪塞患者,孩子们慢慢衰弱、死去——要怪就怪孩子命不好吧。
学生也不会从导师那里得知,其实这种病在国际医学领域已有这样那样的治疗手段,毕竟导师也怕学生举报她见死不救、放任孩子死亡。
医生乙,是某老年病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导大学阀,有真本事,真学问。但他就爱欺压同行、剥削学生,把持研究所和科研团队大权,只手遮天。他想整谁就整谁,他想让谁职称晋升谁便晋升,他想砸谁饭碗就砸谁饭碗。
反腐反到他们单位的时候,平时敢怒不敢言的手下人、同行们,趁机公报私仇,不管某笔陈年旧账是不是他贪的,都扣到他头上……终于,他从这个行业消失了,他领军的科研项目的成员,全部株连,毕竟这么大的数额,不可能是他一个人贪的。于是,此研究项目也从行业消失了。国内有无别的学科带头人,再来重拾研究呢,多少年后重拾研究呢?鬼知道。
以后不幸患上这类老年病的人,只能怪自己命不好。
前天我说到文革期间,迫害科研人员的事,未必全是文盲大老粗干的——其实同行整同行,下手最狠。
同行为什么下狠手整同行,这便是孔飞力在《叫魂》里分析的:在一个高压的社会,人没有法治的、正常的渠道维权,人人都积怨深重,最终演变成一切人对一切人的公报私仇。
没有预警,就像你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遇见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