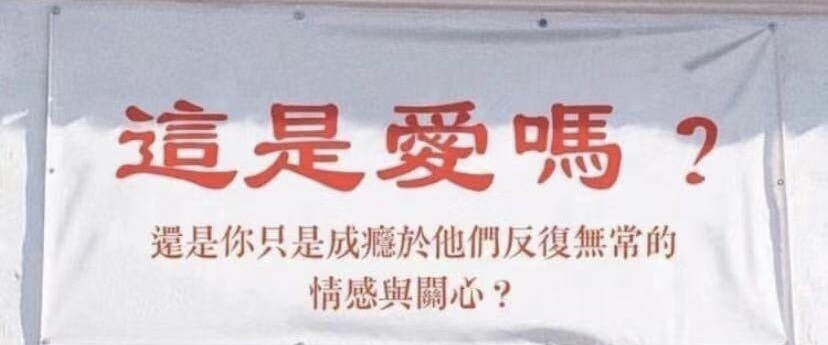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在2015年出版的自传《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Ma vie sur la route)的结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本书献给伦敦的约翰·夏普医生(Dr John Sharpe)。他在1957年——法律允许英国医生出于女性健康以外的原因终止妊娠的十年前——冒了巨大的风险接收了一位22岁、即将去印度的美国女人,为她做堕胎手术。当时他只知道,她取消了在美国的订婚仪式,将要奔赴一种未知的命运。他对她说:“您得答应我两件事。第一,和谁也别提我的名字。第二,这一生,只做您想做的事。”亲爱的夏普医生,我相信深明大义的您,不会埋怨我现在才说出迟到的这句话,在您去世多年之后:
我把我这一辈子活成了我能做到的最好的样子。
这本书献给您。
璀璨只是一瞬,幻灭才是永恒 |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正处在消费主义文化影响下推崇物质享乐的“爵士时代”。面对这个迷茫又混乱、浮华又享乐的年代,菲茨杰拉德一言以蔽之:“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会纵乐、最绚丽的时代,这也是《了不起的盖茨比》所描述的时代。” #掘火档案 | https://www.digforfire.net/?p=7535
我不想以我珍视我写过的东西为耻。我不想以我怀着爱写作,希望得到同等的爱为耻,就算是在我写得不好的时候也一样。我不想以我喜欢人,而且希望和他们交流为耻。我不想以我会因此失望为耻。我不想以我高兴给别人写他们喜欢的东西,因为我自己在一些时候由于抑郁而不想爱为耻。我不想以我迷茫于到底该遵从哪一条道路为耻。我不想以我会因许多事情而愤怒悲伤为耻。我不想以我会把这些声音平静或不平静地发出来为耻。因为这都是自然的感情。
如果我为了能够假装体面地生活,就只好发明一套理论来掩饰它们,那我也不想因此羞耻。但如果我非要拿这套理论,不仅折磨自己,也去嘲笑别人,我心里会觉得我在做没那么好的事。
再如果我缺乏这些正当的感情,却认为这种无欲是比有欲更加正当的,因此把它们拿出去规训别人,我做这样的事是会觉得心里羞耻的。
话说之前因为多囊容易胰岛素抵抗,一胰岛素抵抗就容易得糖尿病去查了一下糖尿病,才知道奶茶喝多(一两天一杯)真的是得糖尿病的一大主要来源。而且不加糖糖分也很高 ![]()
普通人在通缩时期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有1980年之前记忆的、读过相关时代生活过的作者写作的虚构与非虚构作品(非网文,谁拿“穿越七零xxx”这类做参考跟我辩经的我打死谁)的,或者听家人讲过古的,大体都有一点模糊印象。大体是供应不足、购买途径受限、商品质量没有保障、办事难等等。
办事难看起来像是官僚主义作祟,实际上反映的是公共服务的不足。
在眼下这个时代,因为加工制造业还有不同程度的冗余,所以普通人并不会马上感觉到商品供应不足的痛苦。米面糖油有进口补充,服装鞋帽一方面还耐用,所以吃穿真的不是用来探测通缩最灵敏的指针。
最灵敏的指针,来自那些没有什么竞争也谈不上库存的领域: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交通、治安、教育、养老、水电、医疗卫生、环保、垃圾处理。
所以现在你可以自由感受一下了:你收到的服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
没有预警,就像你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遇见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