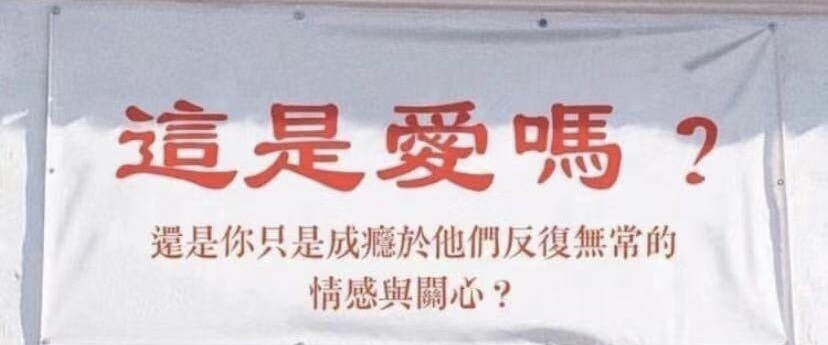
@blessus av编剧
山东某地级市,埃尔文宫斗失败,从党委调到妇联去了,空降了一个吉克带着一个嫡系皮克。兵长本想跟着团长去妇联,被团长握着他的手说李伟,想想人民!此时,市里正在主导一个城建项目,有一大片地面临拆迁,吉皮两人与商业地产企业暗通款曲,希望压低拆迁补偿价格,但兵长想要争取人民的利益。势单力薄的他特聘了本地大学的副教授韩吉作为项目顾问,出具拆迁补偿方案。但到具体商洽的时候,吉克以韩吉是女的不能上桌为由拒绝韩吉参与讨论,会上,文质彬彬的吉克和口笨舌拙的兵长形成鲜明对比,吉克的方案获得通过。兵长想到人民,对吉克更加气不打一处来,对吉克进行质问。想不到吉克以谈谈为名,将兵长约到一家娱乐会所,在兵长酒里下药,并指使三陪女勾引兵长,意图留下兵长嫖娼的照片作为把柄。兵长识破了吉克的诡计,更加愤怒,冲动之下殴打、捆绑并强奸了吉克。事后顺水推舟,拍下吉克的艳照,对吉克进行要挟。吉克有苦难言,只得修改了拆迁补偿方案,给予了人民优厚的拆迁补偿。世事难料,此事作为吉克的政绩,让吉克获得了升迁。升迁后的吉克,桌上竟放着皮克的辞职信,原来皮克在拆迁片区买了五套房,早已财务自由。吉克提了两斤水果,去皮克即将拆迁的住宅中拜访皮克,没想到竟然看到对门走出一个人,赫然是埃尔文,原来埃尔文拉满杠杆,在拆迁片区买了10套
@blessus 那不一定,你喜欢道姑朋友,说不定也喜欢长恨歌的国风歌曲
感觉好多人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在(想象中)保护自己利益的基础上的,他们满脑子觉得天下权与利就是分蛋糕(cake theory):别人得到的多,我就一定得到的少,因此突出一个排他性/exclusivity,所以遇到别人要求基本人权的情况就会首先宣传“如果保护这些人的权益,我的权益就要受损”
殊不知其实很多时候人权这东西是木桶效应(cannikin law):即你的基本人权是由人群中最低人权者的人权水平决定的——因为你也有可能“跌落”,即因为意外变成失权者,或者你也可能在权力价值体系中被定义为失权者,然后你的人权也会被剥夺
你支持对身障人士的权益忽视,可你能保持年轻健康无病无灾一辈子吗?你支持对性少数的仇恨犯罪,但你能保证你在所有仇恨犯罪者眼中都是完美的顺直人吗?你支持对异见者的迫害,可你能保证自己永远是完美的爱国者吗?你支持集中营对少数族裔和少数派进行监禁和惩罚,可你能保证自己不会有站在少数方的那一天吗?
但这些人就是想不明白,觉得铁拳迫害/猎巫时更大可能伤害到别人的话,自己就是安全的,其实不是:只要这种事情不停下,那总有一天轮到你。
我今天突然想明白个事,就是同人(耽美也算)解决了女性浪漫爱情小说的一个千古难题:如何描写(男人的)爱慕。传统异性恋写这个很难,祖师奶奶简奥斯汀都得先写「傲慢」与偏见,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男人不会这样爱女人,他们对异性的爱更像是对小猫小狗那种……怜爱,和某种理所应当的占有(本来女性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男性的私有财产)。就连西方骑士贵妇小说和东方儒家主义,说穿了也是假意,一种居高临下的宠溺,不是真正的尊重——不像,比如说,男人对自己的对手。
“爱慕”是一种非常女性化的爱法,把爱人放到一个比自己更高的位置上,这其中翘楚大概是娇妻文学,把一个一无是处的男人捧上神坛,其本质是弱势群体慕强以寻求权力的保护。但其实相互的倾慕是非常美的,高山流水遇知音,那不就是灵魂正印?同人女写纸片男人做爱或者做恨,底色都是这个。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发自内心地认为两个人互相蔑视对方,也许那样就不值得一操了。
异性恋
昨天和哥打电话,哥说起高中追过他的女同学一个月前突然频繁约高中和他关系好的同学出去玩,大家都很莫名其妙。我略作思考说应该是她要结婚了,怕直接请大家来婚礼收份子钱很突兀,所以先铺垫一下。哥不置可否说你真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别人,说晚安后挂了电话现在都没发消息。太搞笑了我早上答辩的时候想起来都绷不住
说起来,史诗/epic这个文体在华夏文化里似乎是不存在的,而且“史诗”这个翻译也很misleading:epic既不是晚期意义上的“历史”,也不是晚期意义上的“作者诗歌”。我觉得放在欧洲地中海文化lineage里和它更接近的是神话/mythology和古希腊戏剧。它们的共通之处在于描绘的事件和人物(包括神和其它非人精怪)都不是写实主义/realism的,而是高度抽象/符号化的。习惯了晚期写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人会非常受不了它们讲述的故事里看似莫名其妙的逻辑和非常平面化的人物,但那恰恰是它们的重点:故事中的人物并不是真实的人/human,而是某种概念/形象的人形stand-in或者说是archetype,让人物“丰富/复杂”反而会“冲淡/dilute”了他们的对于史诗的作用/strength。古希腊戏剧舞台上演员全程戴面具表演可以说visually向观众强调了这一点。我甚至认为,早期史诗的“功能”之一是在所谓哲学还没有独立出来(并且相应诞生了各种思考工具)之前人们进行某种“哲学思考”的辅助工具,可以说是一种proto-philosophy,人物的“平面化”类似于一种对人的哲学抽象,是能进行哲学思考的必要前提。
而现代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很难再把自己tune到这个状态了(也已经不习惯在哲学之外做哲学思考了)。失败例子比如托尔金的整个中洲系列,宝钻和HoME更接近早期史诗的“平面化”,而魔戒和霍比特人更偏向晚期小说的“立体化”,但两者都处于一种“犹豫不决”中。而且托尔金作为一个现代人当然可以试图写一个新的人类origin story,并且写得符合“长且设定宏大、充满各种英雄事迹”这些史诗的表面特征(或者说现代人使用史诗/epic这个词时的第一联想),但“死亡是神给人类的礼物”、“善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人类/小人物的力量”这些内核没有足够的力量成为支撑起早期史诗的那种哲学backbone。
没有预警,就像你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遇见我
